
王天行,从崭露头角的作品《杀鱼》,充满艺术直觉的《路边野餐》,到担纲摄影指导、获得第37届金鸡奖最佳摄影提名的《孤注一掷》,他的创作始终在“直觉”与“理性”、“艺术探索”与“商业诉求”、“观察者”与“体验者”之间寻找平衡。
平面摄影的敏锐性如何在电影叙事中发生作用?电影中动人的“不完美”如何诞生?从独立创作者到商业片摄影指导是什么样的经历?本期影像环聊,我们和王天行聊了聊他的“创作轨迹”。01
创作中的限制
不全是坏事
孙一冰:我在大学学的也是电影视觉,后面转向了平面摄影。我看你平时也会进行平面创作,但其实拍摄平面的影像和拍摄动态的影像区别还是很大的,这两者在你创作中的边界和融合点是什么?
王天行:对我来说,平面摄影更个人、更独立,很多灵感是在特定情形下被自然触发的,直觉性会强一些。影视摄影大多是先预设再执行,并且要考虑“命题作文”的因素,对理性思维要求很高。
两者的融合点是观察力和对信息量的控制。在平面摄影中,我倾向于信息极简化,摘取现实世界的局部,使氛围优先;而拍电影时,我倾向于内容优先,在镜头中把诸多能增加临场感的元素都拍进去。

当然,拍电影弱情节的部分,比如说留白,或者人物情绪化的东西,不需要讲清楚一些事,只是表达当下的氛围和情绪,我就有机会运用拍照片的思维去拍摄。把拍照的直觉性应用到影视摄影工作现场,会让我快速地获得表达灵感。
孙一冰:影视摄影中的“命题”,是否会对个人创作产生限制?
王天行:会,但有限制并不完全是坏事。以前我希望自己在创作中没有任何限制,去年拍了两个广告,改变了我的想法。广告要求用手机来拍短片,一开始我有点犹豫,但因为导演都是特别想合作的,最后还是接了。
用手机拍短片,这个限制带来一种特别大的好处——当我用摄像机工作的很多手段都消失后,只能聚焦在焦距、构图、光线、色彩等基础要素上,就像在武侠小说里,一个高手和别人比武,发现自己很难打败对方,于是就把眼睛蒙上了,结果一蒙上眼睛,心无旁骛,感官好像都打通了,武力反而变得更高强。

孙一冰:你在早期的作品《杀鱼》中,担任了导演、编剧、摄影等多职,作品有强烈的个人风格,呈现出现实与诗意之间的张力。你是如何确定表达方式的?是如何身兼多职完成作品的?
王天行:《杀鱼》是我的毕业作品。当时预算有限,写剧本时也进入了很长时间的瓶颈期,于是我决定先找想拍摄的故事发生地——这个地方需要有空间上的复杂性,还要具备天然的美学条件。
我去了海鲜市场,看着繁忙来往的小推车,永远湿漉漉的水磨石地面,以及被丢进冰柜的像铁棒一样的带鱼,感受到了诸多有趣的元素,很快就把这些元素串联成了一个故事。
我的剧本是坐在海鲜市场里写完的,市场中的许多元素被意象化,参与叙事,所以影片不只是一个直白的故事,还具有趣味性。例如,短片里的冻带鱼看起来像一把刀,做杀鱼生意的主角最后因鱼而亡,有种宿命感。

其实最后的成片还是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,但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,导演、编剧、摄影、剪辑的工作都在我一个人身上,充满挑战性;团队的成员都是身边的同学、好友,合作默契……
现在我仍怀念这样的“学生气”剧组,感觉大家在有限的条件下,会有更多想法。
就像咱们现在还在拍胶片,那胶片到底哪里好?可能是因为数码的快门可以摁无数次,但胶片的张数一直在倒数,所以拍胶片的时候,每一次按下快门前,你都会想这到底值不值得拍摄?

02
真情实感的瑕疵
胜过工整的技术
孙一冰:我非常喜欢《路边野餐》,它的每一个镜头都很个人化、情绪化。我看到你除了负责摄影工作外,还担任编剧。你是如何与毕赣导演一起完成这部长篇作品的?
王天行:《路边野餐》对所有参与的伙伴来说,都是人生中的一段奇遇。
它不像是工作,也没有很多的世俗诉求。那时候大家聚在一起,年轻又自由,就像一群没长大的小孩在一起玩,没考虑过它未来能不能成为院线电影,也没考虑时间和成本,仅仅是带着对电影的追求去拍这部电影的——我和毕赣导演也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合作。

我们只有一个机位,其实那会儿也不知道要怎么拍,就是非常专注在镜头内,觉得那样拍比较好,更多是靠直觉。当时我和导演经常有一种沟通是,此时此刻我们更想观察谁,摄影机就对准谁。
从摄影的角度来看,《路边野餐》这部电影是感情大于理性,艺术直觉大于技术,实际上技术方面的问题非常多。不过,很久之后我才想明白一件事,真情实感造成的“瑕疵”,也许比工整的技术更能让观众共情。

孙一冰:你之后打算探索其他艺术媒介吗?怎么看待AI?
王天行:目前我只想做好摄影师的工作。
我赞同AI未来会成为很好的工具,但我只会把它当作工具,具体画面是什么还是要自己把控。
我还没看到AI全盘取代摄影的可能性。现在观众看各类短视频的时候会发现,视听语言非常风格化,特别“准确”。如果大家一直看这样的产品,渐渐就会感到索然无味。
人的价值,反而是笨拙和瑕疵。一张战地记者拍的纪实照片,也许构图不好,清晰度不高,但我们可以通过照片感受到这个人的慌乱,看到场景的复杂性。这样的照片和AI生成的照片是完全不同的。

03
拍完一部电影
像经历了一次高考
孙一冰:在2023年上映的商业片《孤注一掷》中,你首次作为摄影指导亮相。你是如何从摄影转变为摄影指导的?摄影指导相对于摄影而言有何不同?拍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?
王天行:我成为摄影指导,主要是通过拍广告。2017至2022年,广告市场很流行拍“微电影”和“剧情广告”,对我来说算是时代红利。那段时间,我拍摄了大量这种类型的广告,也挑战了一些新颖的影像实验,积累了很多拍“商业故事片”的经验。
“摄影”到“摄影指导”的名称变化,更多是代表着制作和团队规模的变化。《路边野餐》的摄影组只有2至4人,所以各位主创都不好意思称自己为“指导”。

而《孤注一掷》的摄影组,加上移动组和灯光组,总人数近60人。拍摄商业片时,团队中配合的人数、不同职能的工种都有很大变化,除了视听塑造能力,也特别考验一个摄影指导的组织能力。
说到印象深刻的经历,拍《孤注一掷》时,正巧遇到出入境困难,但我们的故事又发生在东南亚。于是,从导演到美术指导,都拿出过往在东南亚旅行和工作的资料,最后找到海南儋州这样一个建筑风格和植被样貌都很对味的地方。电影上映后,很多人都不相信影片没有去东南亚取过景。

孙一冰:《孤注一掷》的画面都很好,但是跟《路边野餐》比起来,风格化的东西没那么多。这是不是创作者视角到商业视角的转变?
王天行:如果让我自己创作,作品里会有非常多我个人的特点和想法;但给了要求和题目,就必须先把这些完成。
我拍商业片的时候,“先把商业片拍好”会占据想法的主流。只有商业那部分不需要我非常用力实现的时候,我才会去考虑自己的风格适不适合加入其中。
这也是我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。我的选择是先达到要求,再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。

孙一冰:作为摄影指导拍摄电影和拍摄广告,两者在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感受吗?
王天行:广告是视觉先导,电影是故事先导。拍摄广告时,画面的形式以及如何放大感官感受,是我的首要诉求。拍广告很过瘾,很多形式的美学画面都可以在广告中展现。
至于拍电影,更像是一种视觉翻译,要把剧本中的文字、人物的内心活动等等都通过镜头翻译给观众。通过电影镜头的串联,就像一句一段的话被讲了出来,这是电影摄影的魅力。

另外,广告经常需要快速高效地传递意图,而电影则有很多机会利用更长的节奏来控制影像的起伏,产生耐人寻味的情感力量。
总的来说,拍完一支广告,像做完了一次单元练习;而拍完一部电影,像经历了一次高考,我的情感分量是有区别的。04
我更在意
影像的真实感
孙一冰:不管是拍广告还是电影,拍人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。对于如何拍好人,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?
王天行:我最在意的是让观众感受到人物的视线。人物在看什么,看的情绪是什么?我的镜头会跟随人物的视线选择角度、景别、运镜,这样更容易使观众感知到人物的心理,有代入感和临场感。

另外就是拍摄距离的控制,与人物之间的距离可以传递出人物的处境,也可以丰富观察的视角。
我拍电影会把视角做得特别丰富,不会考虑用什么焦段方便,而是考虑怎么表达更好,所以我大部分时间不使用变焦,就只用定焦。
定焦有一个好处,它会强迫你去改变机位和人物的距离。在同一个位置,觉得人物在画面里不够大、不够满,用变焦当然可以实现效果,但摄像机的位置没变,与被拍者距离还是很远;如果用定焦,换更广的镜头,挪动摄像机,让它离被拍者更近,这个距离感观众是可以感知的。听上去有点笨拙,但这就是人的味道和思考。

孙一冰:除了摄影等视觉艺术之外,你在生活中还有什么兴趣爱好?我看到你经常拍手办,我有一阵子非常喜欢组装高达模型,发现拍好这些模型不是容易的事情,有什么窍门吗?
王天行:玩具和模型是我从小到大的爱好。开始拍广告后,繁重的工作量让我特别需要一个释放的出口,玩这些模型可以让我沉浸在一个很小的世界里。
拍它们的时候,我会从玩具的角度出发,重新构想世界,有点像小孩子的“想象游戏”。我希望呈现一种“小玩具”拍摄“小玩具”的感觉,而不是简单地通过人类视角去拍摄。
我有一个系列是在北海公园的假山中拍摄的,我会把假山想象成星际环境,有两个探险的宇航员在其中探险。

孙一冰:看到你经常在朋友圈发可爱的女儿,有了女儿后,你会开始关注家庭相关的拍摄内容吗?女儿对你的创作心态起到了什么影响呢?
王天行:我原本想保持某种统一的格式,把我女儿的成长过程拍成一个系列,就像川岛小鸟那样,但目前没有做到。
和她在一起的时光,我都忍不住沉浸其中,会放弃拍摄的「作品性」,注重记录。我希望在那些精彩的瞬间中成为体验者,而不是观察者。
有了女儿之后,我会更在意影像的真实感,而不只是画面中的形式和要素。影像传递真实感的价值非常高,具有“让人相信”的力量。

「孙一冰说」
或许是因为我大学学的也是影视专业,和天行聊天总会让我回想起学生时代美好的创作时光。
天行在创作中有股“生猛劲儿”,从《杀鱼》到《路边野餐》,他拍摄的每一帧画面都带有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,让我忍不住反复观看。
他在聊拍摄电影和广告的时候提到了“视线”的概念,给了我很大的启发——或许平面摄影也可以借此来加强“一瞬之间”的人物情绪表达。
 LIUCHUN
LIUCHUN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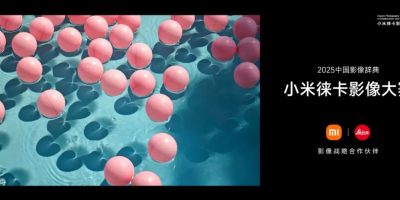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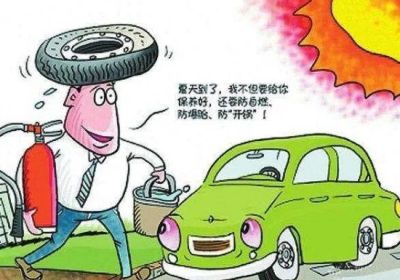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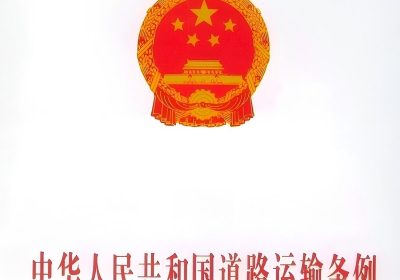

收拾收拾